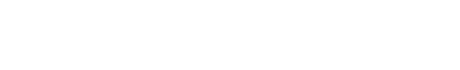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livings)出品。联系方式:/font>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livings)出品。联系方式:/font

这个市场中包含着部分合法的交易需求:医学院的人体材料,使得准医生们能够充分学习解剖学知识;领养机构中的第三世界儿童,成为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发达国家家庭的收养对象;制药公司征集志愿者进行超级药物的检测与试验等等。
但人体市场中的黑色地带则是血淋淋的真相:人类能兜售自己的身体器官,也可以买到需要的任何身体部位,大量器官掮客、人骨窃贼、人口贩子以此获取暴利。印度的“肾脏村”;解剖示范用骨骸由盗墓人从墓园、太平间、火葬用的木柴堆里偷窃人骨制成;寺庙将虔诚信徒的头发卖给假发制造商,年利润达600万美元……在金钱诱惑面前,各样骇人听闻的荒诞悲剧屡禁不止。
记者斯科特·卡尼为调查人体器官买卖内幕,在印度、孟加拉等地居住十年之久,他在《人体交易》一书中记录了全球人体市场地下交易情况,揭露了这一产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地下贸易在历史上的兴衰和复兴,并逐一展现了此产业中盗尸人、代理孕母、人骨贩子和贩卖身体部位维生的穷人群体的真实生存境况。
本文选取书中第七章,讲述了印度边境城镇戈勒克布尔的血液交易情况和地下血液农场的线
印度色彩节的前几天,在闷热的印度边境城镇戈勒克布尔(Gorakhpur),一个瘦削虚弱的男人跌跌撞撞走向一群农夫。他的皮肤苍白,眼睛下垂,两只手臂上有好几排紫色的针孔。
尼泊尔的赤贫情况要比印度更严重,从尼泊尔涌入印度的难民成千上万,戈勒克布尔正是他们的第一站。多年来,无穷无尽的难民苦难故事已经麻木了农夫的同情本能,在农夫的施舍清单上,吸毒者的排名更低。因此当这样的一个男人求农夫给他钱坐公车时,农夫起初并不予理会,但男人不死心,还说自己不是难民,是从“临时监狱”里逃出来的,把他关起来的人抽他的血卖钱。农夫这才放下了原先麻木的情绪,打电话报了警。
过去三年以来,这样的一个男人一直被囚禁在一间用砖块和铁皮搭建的小棚子里,距离农夫喝茶的地方,走路只需要几分钟而已。他手臂上的针孔并不是上瘾造成的,而是劫持者反复用中空注射器扎他的皮肤所致。
劫持者是个残酷无情的现代吸血鬼,但同时也是当地奶农及受人敬重的地主——帕普·亚德哈(Papu Yadhav)。亚德哈之所以监禁那男人,是为了抽取他的血液卖给血库。某次,亚德哈离开时忘了把门锁上,男人这才得以趁机脱逃。
这个瘦削虚弱的男人带警察前往他被关了三年的地方——那是一栋仓促建起的简陋小屋,夹在亚德哈的水泥房子和牛舍之间。铁门上的坚固门闩,挂着一只铜制的挂锁。警方透过厚度四分之一英寸的铁门,听见里头有人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静脉点滴挂在临时的点滴架上,患者着,好像正要从谵妄中恢复过来。五个瘦弱的男人躺在木板床上,几乎抬不起头来,无法向访客招呼示意。屋里的空气很闷热,跟所谓的消毒环境简直是天差地别。太阳照射在他们脑袋上方的铁皮屋顶上,让屋里的热度加倍,有如置身于烤炉里。其中一个男人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天花板,他的血液蜿蜒着通过管子,缓缓流到地板上的塑料血袋里。他已经虚弱得无法反抗。
他身旁有一个皱巴巴的尼龙袋,已装了5品脱的量,里头还有19个空的血袋有待装满。每个血袋上都有看似官方认证的当地血库贴纸,另外还贴有中央监督管理的机构的条码和印章。
而这栋小屋并非唯一的监牢。接下来的数小时,警察突袭了这位奶农的土地上的另外五栋小屋。屋内情景一个比一个糟糕,受害者几乎都是濒临死亡边缘。最后警方总共救出17人,受害者大多瘦弱不堪,被困在医院核发的血液引流设备旁边。
这些遭受囚禁的受害者说,有一位实验室技术人员每周至少替他们抽两次血。还有人说,自己已经被囚禁了两年半。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家血液工厂,其提供的血液占了戈勒克布尔血液供应量的极大百分比,戈勒克布尔的医院之所以能坐拥充裕的血库,全有赖于这家血液工厂。
当晚,警方紧急将受害者送往当地的市民医院治疗。医生说,他们从来没看过这种情形。血红蛋白负责提供氧气给身体各部位,如果血红蛋白浓度过低有一定的概率会造成脑损伤、器官衰竭及死亡。健康的成人每100毫升的血液有14至18克的血红蛋白;然而,这些受害者平均却只有4克的血红蛋白。他们失去了重要的生命液体,濒临死亡,全都皮肤苍白且因脱水而发皱。值班医生苏曼(B.K.Suman)最先接收了这批警方戒护下的患者,“你捏他们的皮肤,被捏的皮肤会一直停留在那里,像是成形的黏土。”
受害者的血红蛋白浓度太低了,但医生同时也担心,要是让受害者的血红蛋白浓度上升太快,可能会出问题。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受害者的身体已经习惯失血状态,为了让受害者存活下来,必须给他们补充铁元素,并辅以放血疗程,不然的话,受害者有一定的概率会因为循环系统含氧量过高而死亡。
这些受害者在遭到囚禁数周后,就因失血而变得虚弱不堪,连逃跑的念头也没了。几位幸存者在警方面前回忆道,原本这里有更多的人,不过,亚德哈一发现捐血者病重到濒临死亡,就会把他们放到公车上载出城外,这样他们的死亡就会是别人的责任了。
亚德哈保留了一丝不苟的分类账本,记录了他卖给当地的血库、医院及个别的医生多少血量,还记录了对方支付的巨额款项。这些记录也让警方容易了解到整个勾当的运作状况。负责该案的戈勒克布尔副警长维希瓦吉·司里瓦司塔(Vishwajeet Srivastav)表示,根据记录,亚德哈最初只是小商家,只经营乳品生意。刚开始,他会在戈勒克布尔的公车站和火车站寻找毒品成瘾者以及有可能捐血的穷人,那时至少是纯粹的交易行为。
他开出一品脱血液3美元的价码,这笔钱可让捐血人购买数天的食物。卖血虽是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却也是轻松赚钱的方法。亚德哈轻松就能卖掉血液,迅速获利,一般血型是一品脱20美元,罕见血型最多可卖150美元。
随着业务的发展,亚德哈厌倦了在城市的交通站点找人,开始为捐血人提供临时宿舍。由于捐血人就住在他的屋檐下,因此他利用胁迫的手段、虚假的承诺和上锁的门来控制捐血人的命运,也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了。
随着血液生意变大,亚德哈需要帮手,便雇用了前实验室技术人员杰扬·萨卡(Jayant Sarkar)。萨卡曾在加尔各答经营一家地下血液农场,但到了1990年代晚期,他被逐出城外。不过当亚德哈和萨卡两人联手经营时,理所当然地成了该区的一大血液供应商。“血液农场”的概念跟亚德哈的牧场很类似,正因为两者紧密关联,因此他也让牛舍和人舍相邻,以节省空间。
在警方初次突袭行动两个月后,共围捕了9人,包括负责监督采血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想赚取额外利润的当地血库秘书、运送血液至戈勒克布尔各处的中间人,以及负责照顾那些血牛的护士。萨卡一嗅出有麻烦,就成功逃出城外,亚德哈则在住处附近被捕,入狱服刑9个月。
我们非常容易就把惨绝人寰的戈勒克布尔血液农场视为单独事件,认为这种反常现象只会发生在文明世界的边缘,跟另外的地方的血液供应并无关联。
但血液农场的存在,恰巧表明了人体市场中的组织流通状况存在着更为深层的问题:只要有热切的、不关心供应方式或者不在乎人体组织来源的买家,那么血液农场就一定会存在;一旦医疗人员什么也不问就愿意付钱买血,肯定就会有人利用这样的一种情况来将利润最大化。全球的志愿捐血体制十分脆弱,供应量只要稍微受到打击,就可能立即引发像戈勒克布尔那样猖獗的商业化盗血行径。
就在亚德哈获释前夕,我抵达了戈勒克布尔,希望能更了解这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如何变得如此轻易就依赖血液农场。这座城市里的诸多过分行为超出了常态的范围,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印度地区一定不是个案。
戈勒克布尔地处印度与尼泊尔的边界,岌岌可危,既是充满混乱污染的新兴工业都市,也是印度乡间特有的贫穷之城,仅有一条铁路线和一条维护不佳的道路连接着戈勒克布尔与邦首府勒克瑙(Lucknow)。
然而,戈勒克布尔仍是一连串密集村落的中心枢纽,堪称世界上乡村地区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在方圆将近一百英里内,戈勒克布尔也是唯一具备都市基础设施的定居点,因此是政府在此设立机构的重要前哨。但是这座城市本质上是一座建立在诸多匮乏之上的城市,既无法为乡村的大片田地提供基本服务,又没有较高的开发概率。
最为匮乏的当属戈勒克布尔那些已不堪重负的医疗设施,对需要医疗的数千万乡村农夫与移民劳工而言,那些医疗设施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医院往往会补贴医药费,有时还会免费治疗,因此吸引了弱势人群前来。以庞大的巴巴兰姆达斯(Babba Ram Das)医院院区为例,即使坐拥将近十二栋建筑物和救护车车队,仍有一排排农村患者等在大门外,其他大型医院的情况更加糟糕。
超量的患者引发了数个重大难题,尤其是血液供应问题。即使是像接生这样的常规手术,也会造成血液需求量增加,在处理需剖腹产的孕妇时,必须至少备有2品脱的血液,以防出现并发症。而来到戈勒克布尔医院的数百万移民,不是已经生了病,就是身体健康情况差到无法捐血,能够捐血的理想候选人实在少之又少。
一场完美风暴就此成形,不当医疗与违反道德的行径相应而生。要当地相对较少的人口自愿捐血来补足血液库存量,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因此医院所剩的选择不多,只能仰赖当地的血液贩子。
从亚德哈的血液农场走约5分钟的路程,就可看到一块蓝白色的霓虹灯招牌高挂着,上头写着“法蒂玛(Fatima)医院”,这是戈勒克布尔五家血库之一。在法蒂玛医院那道由砖块和铁筑成的大门里面,四散着混凝土瓦砾和建筑废料,原来医院正在进行重大修建工程,一片狼藉。
不过,血库太重要了,即使在整修期间也不能关闭或不运作。因此,负责资助施工工程的耶稣会教会也特别确保了血库会先完工。所以现在我得小心避开流浪猫,穿越一堆堆的钢筋、沙土,爬上尚未完工的阶梯,才能抵达血液科。
这个地方摆满尖端仪器:一台零度以下的冰箱,几乎可储存血液达无限久;数台崭新的离心机,可用于分离血液。这个部门是由吉久·安东尼(Jeejo Antony)神父创办的,他负责经营法蒂玛医院,服务当地教区。可是,就算拥有全世界的高科技仪器,也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他们采集到的血液几乎不足以满足这家医院的需求,更不用提市里的医院了。他说,问题就在于印度人大多不会自愿捐血。许多当地人都很迷信,认为失去体液会让自己的余生都虚弱不堪。戈勒克布尔之所以开始依赖职业献血者,这种迷信看法便是原因之一。
“亚德哈仅仅是代罪羔羊,血液交易的背后有更多人去参加了,不只是像他那样的底层人士而已。”当他听到我提起该案时便如此表示。“每一家疗养院,每一家医院,都有中介的存在。医生需要用血时,就会安排妥当。”
他领着我在实验室里四处参观,他说,他从家乡喀拉拉邦搬到戈勒克布尔,是为了要改善人们的生活,可是,现在他不确定自己所创办的自愿献血库是否真能减轻人们的压力,甚至已经有其他人取代了亚德哈那一帮人。
警方逮捕亚德哈一周后,对血库的血液需求量上升了60%。不过,一年后的现在,“需求量已下降”。戈勒克布尔没有新开的血库,也并未突然涌入捐血者,总之血液是从某个地方来的。
(印度戈勒克布尔某家血库的整体血液供应情景。库存量太低,不足以应付那些川流不息前往戈勒克布尔医院看病的患者,令人感到悲哀。为了弥补供应量的匮乏,某位前奶农所组织的犯罪集团开始从公车站绑架男性受害者,强行抽取血液。有些受害者甚至被囚禁了三年多,每周抽血次数超过一次。)

在印度,合法献血的效果跟这世界上的另外的地方略有不同。由于很少有印度人愿意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献血,因此患者需自行提供献血者,把血捐给血库,以换取手术期间会用到的血液品脱数。一旦患者通过朋友获得血液捐赠的积分后,就能取得一单位配对成功的血液,供自己的手术使用。
理论上,这表示亲友必须自告奋勇前来帮助患者,但是,该制度的实行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多数患者不会要求亲友献血,反倒依赖非正式的职业献血者网络,这些人会在医院门口闲逛,愿意献血换得一小笔钱。
安东尼神父说他没办法阻止卖血行为。医院被困在两难当中,拯救手术台上的患者性命,就非常有可能剥削献血者。站在临床角度来看,患者就要死于手术台时,买血似乎是两害取其轻的选择,戈勒克布尔各大医院都有半职业的献血人。他所在的这家医院规模太小,无法吸引半职业的献血人。
戈勒克布尔的市民医院院长帕瑞(O.P.Parikh)医师在这一生中已捐赠了13品脱血液,明年年底退休前还会再捐赠4品脱。不过他是特例,戈勒克布尔市的其他人不会这样热心捐血。帕瑞负责市民医院的整体营运,他说,血液的供应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大家都怕献血。他们不想交换血液,只想购买血液。”只要1000卢比(25美元),就能买到1品脱的血液,所以要找到献血人并非难事。
帕瑞的医院外50英尺处,就是一长条临时茶铺与香烟小贩,他们又兼作血液掮客。我小心探问一位下排牙齿有槟榔渍的男人,他说,我可以去见丘努(Chunu),那个人是当地的职业献血人。他在送我走之前,还特地警告我:“你一定要在血库那里以血易血,他有艾滋病毒,血液不一定会筛查。”
5分钟后,我就在医院的后巷里见到了一个身形矮小的蓄胡男人,他用披巾遮住脑袋和耳朵。我跟他说,我需要尽快取得一品脱B型阴性血液。
“B型阴性很少见,现在也特别难找到,”他说,“我们大家可以弄到,可是必须从法扎巴德或勒克瑙送过来。”这两个地区首府距离此处约有100英里远。他说,付3000卢比就能安排——这金额很高。我跟他说,我会考虑看看,然后就离开了,他则继续在医院大门外跟其他顾客讲话。
同一时间,在市民医院的血库里则是一幅无助的景象。钢制冰箱里的血袋存量就要空了,只有三袋可用于输血。血库的主任辛格(K.M.Singh)表示:“昨天有人过来,想买血液,我们不得已拒绝。我告诉对方,血液是非卖品,必须献血才能取得血液。对方离开了,不过一小时后,却带着献血人回来。我无法得知他们是不是付了钱给那个人。”
戈勒克布尔的五家血库只能满足一半的需求。患者要负责提供自己的血液供手术用,有时甚至不知道买血是犯法的行为。
巴巴拉赫达斯医院(Baba Raghav Das)的产科病房,堪称戈勒克布尔最大的政府医疗机构,亦是一处把生命带到这世上的凄惨之地。巨大的凸窗上涂了一层半透明的绿漆,大概是为减少刺眼的阳光,却让混凝土病房里充满病恹恹的光线名妇女,她们仍旧穿着从家里带来的衣服,在窄小的病床上等待剖腹产的伤口复原。有的妇女有床可躺,有的则不得不斜倚在水泥地上。病房里还有数十名新生儿,但说也奇怪,没一个在哭的,仿佛这间如山洞般的病房吞没了所有的声音。
一名悉心照料女婴的妇女理了理自己的袍子,接着取出自己的导尿管,让浓汤似的红色混合物流入床下的垃圾桶里。尽管环境看来很糟糕,但是巴巴拉赫达斯医院可以让这些妇女看医生,这是难得的机会。要获得医疗救助,住这种病房仅仅是这些人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有一位叫做古丽亚·戴维的妇女,就住在隔壁的比哈尔邦的农村里,她担心自己在生产时可能会有并发症,便跋涉一百多英里的路途来到这里。
某位未向她透露名字的医生,总共才花了五分钟的时间替她看诊,然后便说她必须剖腹产。他说,作为预防的方法,院方需备有1品脱的血液,患者支付1400卢比(约30美元)的话院方就可安排捐血人。她说:“事情很简单,我们甚至不用多想些什么,医生就会安排妥当。”
对于捐赠者与受赠者而言,依赖职业献血人都是很危险的行为。买血行为不仅会创造商业诱因,造成道德标准降低以提高血液供应量,还会降低血库的整体血液品质。英国社会学家蒂特马斯在《赠与关系》一书中,探讨了欧美血库里的肝炎传播情况,还预见了国际血液供应会受到病毒(如艾滋病毒)的污染。根据他的推论,如果血液的交换只仰赖利他主义,则有可能助长人体组织交易的黑市。此外,经济诱因有一定的概率会让人们被迫做出不负责任的医疗决策。
我在市民医院外头碰见的卖血者,只要能赚到一点点现金,就愿意把据传感染艾滋病毒的血液卖给过路人。因此,不难预见血液供应监管的失败,有可能会助长流行病的扩散。
直至1998年,卖血在印度地区不仅是合法行为,而且也是主流职业,背后有强大的工会和商业捐赠者权利组织支持。不过当印度转向全面的自愿捐血政策后,血液价格便开始高涨,从1品脱5美元涨到将近25美元,对于许多一般患者而言,简直是高不可攀的天价。
虽然法律规定买血属于非法行为,但是印度政府没有能力建立替代的制度,缺血问题扩大到所有依赖稳定供血的医疗产业。血液成分,包括红细胞以及用于阻止血友病患者失血的凝血因子的需求量呈现爆炸性的增长,迫使印度最后不得不开始每年从国外进口价值7500万美元的血液成分。
印度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可管理医疗服务买卖的法律规定,而是在以符合道德的方式或规模采血来满足印度的血液需求量方面,几乎毫无计划可言。合法授权和警方优先事项之间的真空状态,造成医疗黑市趁机兴盛起来。
戈勒克布尔的自由放任市场,只是极端的例子,展现了全球范围内私人医疗与公共医疗之间的根本冲突。美国从罗斯福新政的公费医疗制度,转型到二战后占主导的营利模式时,也发生了极为相似的情况。
美国在1950年代以前,多数医院是慈善机构,往往隶属于政府之下。医药费是由政府自掏腰包全额支付,或予以巨额的补贴。营利性医疗与私人保险并行的时代,要等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后才开始。医疗机构已经知道有些人宁愿支付额外的费用,获得更精细的照护。大型公共医疗机构大多雇用一般从业人员,私人医院则雇用拥有稀缺商品的专科医生,并开始取代公共机构。
血液供应的状况也经历了类似的管理变动。二战期间,前线士兵需要大量血液,以促进伤口痊愈。但是全血很容易腐坏,在跨大西洋的航程中无法保存。为了寻求替代方案,红十字会促进了离心机技术的普及,让红细胞从血浆中分离出来。虽然血浆不含血红蛋白,但是在手术期间,患者的循环系统就能获得所需的血浆血量,而且在治疗流血的伤口时,这种血浆也是关键因素。
血浆的保质期比全血长,而且在长途的海外航程中,完好保存的机率也更高。这种血浆让美国人自愿捐赠大量血液,美国国民更觉得捐血是为了拯救前线士兵的生命。美国与英国本土在战争期间对援助军队所做出的努力,让蒂特马斯有了灵感,他写道,在国家面临存亡关头时,捐血者通过捐血行为拥有了使命感和团结感。
在战争期间,外科医生在动手术时已习惯有大量血液备用,因而发展出更复杂的外科技术,外科领域获得了大幅的改进。到了战后,血液需求量仍居高不下,是因为医生把战场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在民间。不过,少了战争这个因素后,就难以维持高库存量,因此美国需要更有效的采血制度。
1940年代至1960年代期间,有偿的采血中心与无偿的自愿捐血处不稳定地并存,而且有着很明显的阶级差异。有偿的采血处大多设立在贫民区,而自愿捐血处则是在教堂举办捐血活动,并在市区里比较体面的好区设立迎宾中心并维持运作。
在品质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有偿捐血人是基于金钱动机才卖血,并不在乎自己的血液是否安全,只在乎捐血后会收到钱。此外,采血处对于清洁度也很马虎。有偿捐血人的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率较高,那些依赖营利性血库的医院,经由输血促进了肝炎的传播。
在人们自愿捐血的情况下,肝炎案例大幅度降低。当时负责报道血库的记者指出,营利性捐血处环境十分简陋,有时是泥土地面,墙壁摇摇欲坠,“地上爬满了虫”。这类捐血处的重心在于采血,而不是捐血者的健康状况。
即使营利性血库卖的是受感染的血液,也是在赚钱,可是品质的差异引起了医生的注意。在部分城市,医生对于受感染血液所带来的风险感到忧心忡忡,便开始指示医院只购买自愿献血的血库的血液。
营利性血液中心也察觉到这样的做法会危及其经营模式,于是开始反击。私立的血库有计划地控告医院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他们主张血液是公开买卖的商品,因此自愿捐血构成了对原料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显然,医生的临床决策使得患者健康与公司利益产生了冲突。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1962年的堪萨斯城案,当时有两家商业血库把官司打到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那里,并打赢了,因此非营利性医院开始被禁止使用自愿捐血者的血液。在判决书中,医院若继续依赖较安全的血液供应,一天就要被处以5000美元的罚款。
联邦贸易委员会所做出的多数裁决中指出,非营利性的社区血库(Community Blood Bank)以及医院、病理学家和医生,“非法地共谋,以阻止全体人类血液的贸易”。
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医学学会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先前的判例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最终推翻了该项判决。不过,医界许多人仍惦记着之前的裁决,他们提出警告说,医药的私有化会在其他的人体组织交易市场造成类似的问题。他们忧心,商业压力会诱使医生提供不必要的治疗。
在堪萨斯州的血库争取销售商业献血人血液的权利的同时,阿肯色州的惩教署则跟制药公司和医院签署协议,销售从囚犯身上取得的血浆。这项方案有助于补贴监禁囚犯的费用,还能增加阿肯色州的血液供应量,可是没想到最后付出的代价却很高。
在监狱体制里,基本上没有动力去筛查捐血者的血液品质,于是在实施该体制的30年间,阿肯色州的血液造成了肝炎的爆发,也促成了艾滋病毒的早期传播。阿肯色州血液的最大买家之一是加拿大的一家血液供应公司,此公司隐瞒血液来源,借以增加血液销量。而世界各地的买家在不知道血液来源的情况下,进口了带有疾病的血浆,受感染的血液最远遍及了日本、意大利、英国。
最后,美国与加拿大限制了这样的做法,1994年,禁止器官贩运的统一法通过将近10年后,阿肯色州成为美国最后一个明确禁止贩卖囚犯血液的州。根据后续调查的保守估计,光是加拿大境内就约有一千人经由受污染的血液感染了艾滋病毒,另有两万人罹患丙肝。
从世界另外的地方的情况去看,戈勒克布尔发生的事情其实并非反常现象,而是重现早期的血液丑闻。当某个地区缺血时,非常容易就会发现缺血问题已蔓延至整个医疗体制。即使在亚德哈犯下一连串罪行之后,极端的缺血状况也足以诱使别的类型的犯罪计划兴起,借以提升整体供应量。
(在戈勒克布尔的席拉医院地下室里,实验室工作人员展示着一整袋血液,这是他们前一阵子向当地五家血库之一收得的。拍摄这张照片的一个月前,附近村庄的一位农夫向警方报案,说这里的医院员工绑架他,强行抽取他的血液。)
古丽亚·戴维生孩子的那家公立医院,起码要看起来合乎规范一些。然而,私人诊所可就没有这样的限制了。戈勒克布尔只有三家公立医院,民众要是有一点钱,想获得更快(

戈勒克布尔的医疗基础设施像是个大杂烩,掺杂了不公开的秘密诊所以及私立医院,宣传廉价药物的广告一排排地贴在每一个街区,如藤蔓般攀上交通标志杆和路灯。戈勒克布尔邻近尼泊尔边界——而尼泊尔的医院比印度的更糟糕,因此走私者和患者会携带大量药物回到尼泊尔。因此从数量来看,戈勒克布尔售卖的药物数量超越了新德里。
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大同小异,私人诊所的品质却有着天差地别。声誉优良的诊所门外,包着头巾的农夫及其瘦弱的妻子大排长龙,甚至长到要绕着街区蜿蜒下去。他们会排上一整天,只为了等来受人敬重的临床医师看病。
至于其他的诊所,常常就连一天要吸引到一位患者都是困难重重。在许多情况下,诊所间为了抢患者而诉诸暴力一触即发。
凯达·奈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一生中大多时间住在喀瓦汉(Kutwahan)这个小村子里,在一小片土地上种植稻米、芒果和香蕉。60年来的辛勤劳作,使得他的脸庞历经风霜,布满皱纹。他的三个儿子都已经前往遥远的孟买当建筑工人,每个月会把一小笔钱寄回家乡贴补家用。奈斯生活节俭,还会储存东西,以备将来老得无法耕作田地时使用。
我跟这位饱经风吹日晒的农夫会面时,他扎着白色的长缠腰布,戴着被太阳晒到褪色的头巾。他的双手因老迈而多瘤节,眼神却充满生气有如年轻人。
他身体有很多毛病,每个月都要坐破旧的公车去戈勒克布尔一趟。他的医生查克拉潘尼·潘迪(Chakrapani Pandey)经常在美国巡回演讲,但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服务穷人,还在戈勒克布尔市中心经营一家诊所,大量补贴穷人的医药费。他是戈勒克布尔最受人敬重的医师之一。每天早上,在诊所开门营业的3小时前,患者就会开始排队,等候接受他的医疗服务。
2009年3月的某天,奈斯照例在公车站搭了电动三轮黄包车要去潘迪的诊所,但没料到司机另有盘算。待奈斯一坐上后座,两名牙齿有槟榔渍、表情凶狠的壮汉便跟他说,他们要带他去看更好的医生。他们跟奈斯说:“潘迪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席拉医院的医生更好。”
当他试图反抗时,那两个男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压制住他。奈斯大喊救命,但没有人听见。
席拉医院跟许多新设立的私人诊所一样,专为离乡背井的劳工提供医疗服务。医院有四层楼,内有候诊室和手术室,提供各种综合医疗服务,不过也跟戈勒克布尔的另外的地方一样,经常发生血液不足的状况。
奈斯说,他被拖到医院前的水泥坡道,最后不得不进了医院,在柜台付了费用。然后,那两个男人把他拖到一间有铁门的隐秘小房间里。他一脸气愤地说:“那里有四个男人,他们分别压住我的四肢,我无法反抗。”
其中一位助手把针他的手臂,然后把一品脱的血液抽到了玻璃容器里。抽血完毕后,他的白色长缠腰布沾了血,接着他们给了他一张治疗尿路感染的处方签,就把他丢到了街上。
因为一直奋力逃脱,加上过度失血,他呈现出半昏迷的状态。将近一个小时后,他的脚才有了力气。等他终于站了起来,就叫了黄包车,前往潘迪的诊所。
身材魁梧、表情和蔼的潘迪医生坐在巨大的铁桌后面,天花板上的灯靠一条细细的白色电线悬挂着,那灯的高度低于他的眼睛。房间内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巨大的冷气机,猛吹出冷风,让诊所的温度接近北极。
“你看到诊所外面大排长龙了吧,在戈勒克布尔,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很受欢迎的医生。但是,我一天至少要损失三名患者,我的患者被其他医院的中介拉走,那些医院想要增加业务量。”
他还说,戈勒克布尔的医院不仅在血液供应方面相互竞争,还会争夺尚有余温的患者尸体。他们雇用计程车司机和手段不高明的恶棍监视其他诊所,把患者带去那些付佣金的医院,有时会用暴力手段胁迫患者去。
有一次他还抓到了一个中介,对方跟他说如果找到了可能付给医院大笔费用的痛苦患者,佣金最高可达3000卢比(75美元)——这一大笔钱足以让坐计程车这件事变得危险重重。
点击此处阅读网易“人间”全部文章关于“人间”(the Livings)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写作计划、题目设想、合作意向、费用协商等等,请致信:/font>